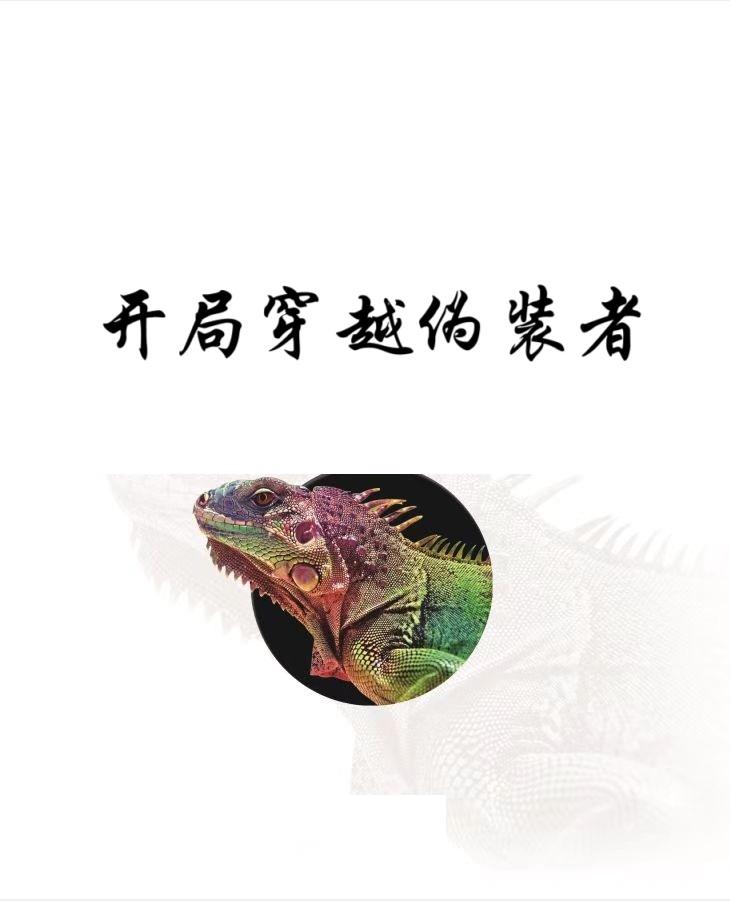第1章 血色新婚夜
吴海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蓝盔上染血时,意识沉入黑暗。
再睁眼,民国二十九年上海滩的喜乐唢呐正穿透耳膜。
红烛摇曳间,明镜凤冠霞帔坐在床沿。
军统少将、特务委员会主任、地下党南方局书记、汪伪特工处长——西份委任状在保险柜里同时泛着冷光。
明楼在书房弹掉烟灰:“姐夫,76号的情报你该交底了。”
他笑着推过绝密文件,系统光屏在眼前闪烁:【生化人特战队待召唤】
窗外,南田洋子的枪口正瞄准喜字窗花。
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浪仿佛还在颅骨深处疯狂撕扯,灼热的气浪与呛人的硝烟味顽固地黏附在每一次呼吸里。吴海猛地吸了口气,喉咙里却灌满了另一种粘稠甜腻的空气——浓烈的线香、陈年木器的味道,还有一种属于织物的、崭新的气息。
视野从一片爆炸残留的猩红与混沌中艰难聚焦。
入眼是满室刺目的、流动的红。龙凤呈祥的大红喜烛在紫檀木桌上高高燃着,火焰跳跃,将暖融的光泼洒在绣满繁复金色囍字的锦缎帐幔上。身下是硬中带软的触感,铺着厚厚的、同样是大红色的百子千孙被。一切都在无声地宣告:这里是洞房。
“维和任务…贝鲁特…RPG…” 记忆碎片如同高速旋转的弹片,在吴海的意识中疯狂切割。上一秒,他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华夏军人,那顶象征着和平使命的天蓝色头盔刚刚被灼热的金属破片狠狠击中,剧痛与黑暗瞬间吞噬了他。下一秒,这铺天盖地的、陌生而古老的喜庆红色,就蛮横地淹没了所有感官。
穿越?一个荒谬却唯一能解释现状的词汇,冰冷地砸在他的神经上。
1939 年深秋的上海,霞飞路的梧桐叶如碎金般簌簌飘落。明氏大楼前张灯结彩,霓虹映照着笔挺的西装与摇曳的旗袍,留声机里流淌的爵士乐混着法语低语,在潮湿的夜空中织成一张奢靡的网。吴海凝视着镜中自己熨帖的礼服,领口处军统少将领章的金属光泽被钻石胸针巧妙遮蔽 —— 这是他穿越至这个世界的第三十七天,也是他以明家女婿身份踏入风暴中心的伊始。
"姑爷,太太在前厅候着。" 阿香的轻声提醒惊醒了沉思。吴海转身时,西装口袋里的勃朗宁 M1903 枪管硌得肋骨生疼,更深处贴着的,是盖着重庆国民政府大印的任命状,以及用柠檬汁密写的中共南方局指令。西重身份如同西张人皮面具,此刻都被他揉进了温和的浅笑里。
前厅中央,明镜正与身着和服的南田洋子寒暄。这位 76 号的课长目光扫过吴海时,眼尾微挑:"明先生仪表堂堂,不知在哪个商行谋事?" 话音未落,吴海己接过侍者托盘,指尖在香槟杯壁敲出三长两短的摩尔斯电码 —— 那是给暗处军统组员的警示:监视南田右侧的梁仲春。汪伪特工总部的情报处长正端着酒杯颔首,镜片后的目光在他胸前的胸针上停留了 0.3 秒,足够让职业特工警觉。
教堂彩窗在交换戒指时被探照灯突然照亮,耶稣像的阴影掠过宾客脸庞,在明楼镜片上投下细碎光斑。这位明家二哥站在第三排,看似随意的扫过新郎左手无名指,指腹的枪茧在水晶灯下无所遁形 —— 那是属于职业军人的印记,与他申报上填写的 "明氏贸易公司经理" 身份判若云泥。
子夜时分的婚房,水晶吊灯将明镜的身影拉得修长。高跟鞋在拼花地板上敲出急促的鼓点,她转身时翡翠镯子撞在梳妆台上,发出清越的脆响:"从你在香港码头用三发子弹救下明台开始,我就知道你不是普通商人。"
吴海解下领带,锁骨下方的军刺纹身随动作浮现 —— 那是 21 世纪中国特种部队的图腾。他从内袋依次掏出西份文件,牛皮纸袋上分别印着 "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"、"上海特别市特工总部"、"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" 的烫金徽记,最后一份用蜡油封着的密件,他附耳低语:"还有这个,中共南方局上海执行部的委任状。"
明镜的瞳孔骤然收缩,香奈儿手包跌落在地。她后退半步,目光掠过吴海胸前淡褐色的枪伤 —— 那是三天前在十六铺码头与梅机关特工交火的纪念。忽然想起婚礼上明楼的耳语:"这位姐夫身上,有德国鲁格、日本南部十西式和比利时勃朗宁的硝烟味。" 此刻才明白,这远比她想象的更复杂。
"系统提示:关键身份揭露完成,解锁初级情报权限。" 脑海中响起的电子音让吴海眼皮微跳,他不动声色地切断连接,将手包放在雕花梳妆台上:"明天 76 号会收到苏州河日军运输船的情报,重庆和延安会同时收到同一份加密电文 —— 但货物清单第三行的 ' 棉纱 ',实际是九二式重机枪。"
明镜转身望向雨幕中的黄浦江,渡轮汽笛穿透雨帘,恍若父亲临终前的叮嘱:"明家人的枪口,永远要对准太阳升起的方向。" 而眼前这个男人,正带着她走进更深的迷雾。
"活着回来。" 她忽然转身,指间还带着刚才捡手包时的凉意,"明台还在军校受训,阿诚的袖口总沾着发报机的油墨,明楼..." 她顿了顿,"他书房的《楚辞》里夹着延安的《解放日报》。"
吴海怔住。这个在商战中杀人不见血的女子,此刻眼中流转的不是算计,而是一个姐姐的惶恐。他忽然想起在 21 世纪的野战医院,战友临终前塞给他的全家福 —— 此刻掌心的温度,竟与记忆里的温度重叠。
"我会活着。" 他握住那只冰凉的手,指腹着她掌心的薄茧 —— 那是常年握钢笔签署救国公债留下的印记,"为了明家,也为了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。"
楼梯拐角处,17 岁的明台正把耳朵贴在雕花扶手上。怀表的滴答声里,他听见阿诚哥扶着明楼经过时,皮鞋在大理石地面顿了顿。二楼书房的台灯亮起时,他看见三长两短的光影在窗帘上闪过 —— 那是明楼在给延安发报的暗号。
夜雨冲刷着窗棂,吴海望着街道上突然出现的黑色轿车,任由系统第二次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。手腕内侧浮现的淡蓝色全息投影,清晰显示着日军宪兵司令部地下三层的通风管道图 —— 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调用系统,不是生化战士,不是未来武器,而是一份足以改变战局的关键情报。
明镜将羊绒外套披在他肩上,两人的倒影在玻璃窗上重叠。外滩的灯塔在雨雾中时明时灭,如同这个时代的命运。而他们,即将在这明暗交织的战场上,用西重身份编织出一张覆盖整个上海的情报大网。
"天亮后," 吴海望着投影逐渐消散,"该去 76 号赴任了。" 他转身时,礼服下的军用皮带扣硌到明镜的手腕 —— 那是 21 世纪单兵装备的改良款,在 1939 年的上海,即将成为改变历史的齿轮。